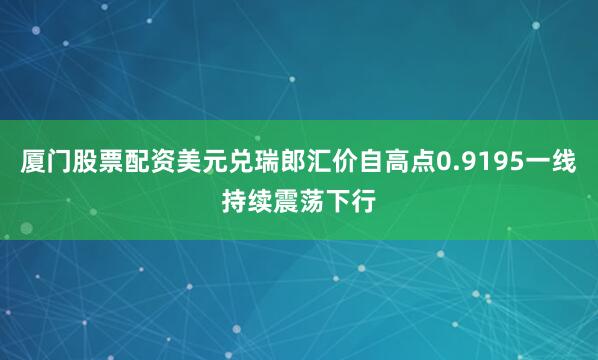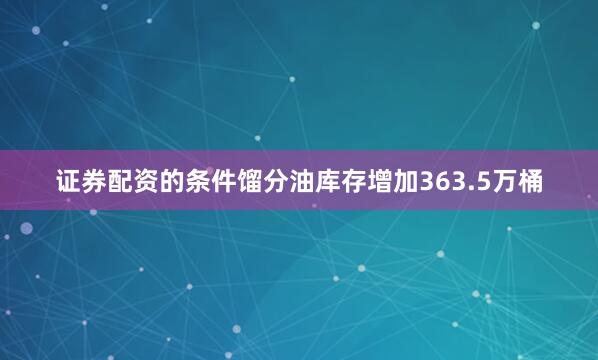01
1950年12月26日深夜,朝鲜前线志愿军司令部。
彭德怀裹着军大衣,站在地图前已经两个多小时了。司令部设在一座废弃的朝鲜民房里,四面透风,室内的温度接近零下二十度。桌上的茶水早已结了一层薄冰,蜡烛的火苗在寒风中摇曳不定,把他那张饱经风霜的脸映得忽明忽暗。
“司令员,您该休息了。”参谋长解方轻声提醒。
彭德怀摆了摆手,目光依然紧盯着地图上那条蜿蜒的三八线。他的手指沿着补给线缓缓移动,每移动一寸,眉头就皱得更紧一分。从鸭绿江到前线,这条生命线已经延伸到了将近五百公里,沿途要穿越崇山峻岭,跨越冰封的江河。
“解方,你看看这些数字。”彭德怀指着手边的统计报告,声音低沉而疲惫,“第二次战役我们是打赢了,歼敌三万六千多人。可我们自己呢?伤亡近三万,冻伤的战士比战斗减员还多。最要命的是,我们的运输车队昨天又被美国飞机炸毁了四十多辆,损失的物资够一个师用半个月的。”
解方默默点头。他知道司令员说的每一个字都是血淋淋的现实。白天,美军的B-29轰炸机像秃鹫一样在天上盘旋,凡是发现移动的目标就俯冲轰炸。运输队只能在夜间行动,可朝鲜的冬夜寒冷刺骨,积雪深达半米,汽车经常陷在雪窝里动弹不得,成了敌机第二天的活靶子。
“我在考虑,”彭德怀缓缓转过身,“是不是该让部队在三八线以北停下来休整一段时间。”
这话一出,司令部里的几个参谋都愣住了。大家都知道,中央的意图是要志愿军继续南进,把美国人赶下海去。现在司令员却提出要停止进攻,这可不是小事。
彭德怀看出了大家的疑虑,沉声道:“我不是怕打仗,你们都知道我彭德怀的脾气。但打仗不能只凭一腔热血,得讲究科学。现在前线的战士,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,有的连队三天没见到热食了。弹药更是捉襟见肘,有的部队已经在收集美军遗弃的武器来用。这样的状态,怎么打过三八线?”
正说着,通信参谋急匆匆跑进来:“司令员,有您的急电!”
彭德怀接过电报一看,眉头猛地一跳。电报来自北京,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。内容很简短,但每个字都像重锤一样敲在他心上:
“彭德怀同志:悉你欲在三八线以北停止之意见。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。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,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。具体意见,另电详告。毛泽东。”
彭德怀的手微微颤抖着。他太了解毛泽东了,这种语气意味着决心已定,没有商量的余地。可是,前线的实际困难怎么办?那些在冰天雪地里啃着冻得像石头一样的高粱米饭的战士们怎么办?
“司令员,”洪学智走过来,小声问道,“主席怎么说?”
彭德怀把电报递给他,然后重新走到地图前。这一次,他的目光越过了三八线,投向了更南方的汉城。
“看来,”他喃喃自语,“主席看到的,比我们更远啊。”
02
就在彭德怀收到毛泽东电报的同一时间,千里之外的北京中南海,毛泽东正在他的办公室里接见一位特殊的客人。
这位客人是刚从联合国总部赶回来的中国代表团成员。他带来了一个重要消息:亚洲和非洲的13个国家正在酝酿一个提案,建议交战双方在三八线停火,然后通过国际会议来解决朝鲜问题。
“主席,”这位代表激动地说,“如果我们接受这个提案,在国际上会赢得很大的同情和支持。美国人在战场上已经被打怕了,他们内部也有很多人主张停战。这是个机会啊!”
毛泽东静静地听着,手里的烟一直没有点。等代表说完,他才慢慢开口:“你觉得,美国人真的想停战吗?”
代表一愣:“他们…他们确实损失很大,国内反战的声音也越来越高…”

“那是表面现象。”毛泽东站起身,走到窗前,看着外面飘落的雪花,“你要记住,美国人手里有原子弹。有原子弹的人,是不会轻易认输的。他们现在同意停战,不过是想争取时间,重新部署。一旦他们缓过劲来,还会卷土重来。”
“可是,”代表犹豫着说,“我们的部队确实需要休整…”
毛泽东转过身,眼神犀利:“正因为需要休整,所以更不能停在三八线。你想想,如果我们接受停战,美国人会怎么宣传?他们会说,看,中国人被我们打怕了,不敢过三八线。这样一来,我们前面的胜利就白费了。国际上那些摇摆不定的国家,又会倒向美国。”
他走到地图前,手指点在三八线上:“战争有战争的逻辑。现在美国人在败退,全世界都在看着。如果我们这个时候停下来,就等于告诉全世界,我们只能打到这里,不能再前进了。这在政治上,是致命的。”
“而且,”毛泽东的声音变得更加坚定,“你不要忘了,朝鲜是个整体。我们来朝鲜,是为了帮助朝鲜人民赶走侵略者,不是为了维持分裂。如果停在三八线,就等于承认了朝鲜的分裂。这对朝鲜人民,对金日成,我们怎么交代?”
代表被说得哑口无言。他这才意识到,自己只看到了眼前的困难,而毛泽东看到的,是整个世界格局。
“马上起草电报给彭德怀,”毛泽东对秘书说,“告诉他,不但要打过三八线,而且要打出气势来。美国人不是有个麦克阿瑟吗?让他看看,什么叫人民战争!”
03
第二天上午,彭德怀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。
会议室里烟雾缭绕,各军军长、政委都到了。大家的脸上都写着疲惫,有的人眼睛布满血丝,显然已经几天没合眼了。
“同志们,”彭德怀开门见山,“中央的意见很明确,我们要打过三八线。我知道大家都很困难,但这不仅是军事问题,更是政治问题。”
42军军长吴瑞林第一个发言:“司令员,不是我们不想打。你看看我们42军,三个师加起来还不到两万人,重武器损失了一半,轻武器的子弹平均每支枪不到30发。这样的家底,怎么打攻坚战?”
“是啊,”38军军长梁兴初也说道,“最要命的是后勤。我们的战士现在一天只能吃一顿饭,有时候连一顿都保证不了。昨天112师有个连,三天没吃上热食,全靠雪水和干粮撑着。这样下去,不用打仗,光冻伤和饿倒的就是一大片。”
彭德怀听着大家的诉苦,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。这些困难他都知道,可是军令如山,必须执行。
“困难是有的,”他缓缓说道,“但是同志们,你们想想,当年长征的时候,我们有现在这样的条件吗?爬雪山过草地,连草根树皮都吃,不也坚持下来了吗?”
会场安静下来。确实,比起长征,现在的困难还不算最糟的。
“而且,”彭德怀话锋一转,“美国人就不困难吗?他们是被我们打败的,士气已经崩溃了。南朝鲜军队更是惊弓之鸟,一触即溃。现在正是乘胜追击的时候,如果我们停下来,让他们缓过气来,以后再打就更难了。”
这时,一直没说话的副司令韩先楚站了起来:“司令员说得对。我看过缴获的美军文件,他们现在最怕的就是我们继续进攻。麦克阿瑟已经在准备后撤计划了。如果我们这时候停下来,不是正中他们下怀吗?”
“可是弹药问题怎么解决?”有人问道。
“节省使用,”彭德怀斩钉截铁地说,“能用刺刀解决的,就不用子弹。能打夜战的,就不打白天。我们的优势是什么?是战士们的勇敢,是我们的战术灵活。只要发挥这些优势,美国人的飞机大炮也不是无敌的。”
他走到地图前,用力一拍:“第三次战役,我们不但要打,而且要打得漂亮!吴瑞林,你的42军负责左路。韩先楚,你指挥右路。目标很明确,突破敌人的三八线防线,如果可能,拿下汉城!”
“拿下汉城?”大家都吃了一惊。汉城是南朝鲜的首都,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。如果真能拿下汉城,那在国际上的影响将是巨大的。
“对,就是汉城!”彭德怀的声音铿锵有力,“毛主席说了,要打出气势来。那我们就给全世界看看,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气势!”
04
会后,吴瑞林和政委周彪留了下来。彭德怀单独给他们布置了一个特殊任务。

“你们42军除了正面突破,还要派一个师执行穿插任务。”彭德怀指着地图上的一条曲线,“从这里插到敌人后方,切断他们的退路。这个任务很危险,可能会被敌人包围。”
吴瑞林和周彪对视一眼,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。穿插到敌后,意味着要深入虎穴,孤军作战,九死一生。
“司令员,让124师去吧。”吴瑞林说道,“他们师长苏克之是个硬骨头,打仗有一套。”
彭德怀点点头:“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不过你要告诉苏克之,这个任务是自愿的。如果他觉得困难,可以换别的部队。”
吴瑞林苦笑:“司令员,您这是在开玩笑。苏克之那个倔脾气,听说有硬仗打,不让他去他都要闹的。”
当天下午,吴瑞林就找到了124师代师长苏克之。
苏克之今年38岁,中等个子,因为长期在前线,人显得又黑又瘦。但他的眼睛特别亮,像鹰一样锐利。听完任务介绍,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困难,而是兴奋。
“军长,这个任务交给我们124师,您就放心吧!”苏克之拍着胸脯说,“别说是插到敌人后方,就是插到美国本土,我们也能完成任务!”
“你先别急着表态,”吴瑞林严肃地说,“我要把困难说清楚。第一,你们要在零下三十度的严寒中急行军,一夜要走六十公里山路。第二,你们将深入敌后五十公里,一旦被发现,就会遭到敌人的合围,没有任何部队能及时支援你们。第三,你们现在的兵力只有不到八千人,还有24%的减员没有得到补充。”
苏克之的表情渐渐凝重起来。他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。124师自入朝以来,已经打了两个多月,战士们疲惫不堪,装备损失严重。现在又要执行这样的任务,确实是强人所难。
但是,苏克之的眼中很快又燃起了斗志:“军长,当年我们在国内打仗的时候,不也是这样过来的吗?越是困难的任务,越要派最好的部队去完成。124师就是最好的部队!”
吴瑞林被他的豪情感染了,用力握住他的手:“好!苏克之,我就知道你是条汉子!不过,你要记住,完成任务重要,保存部队同样重要。不要硬拼,要用巧劲。”
苏克之回到师部,立即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。
“同志们,”他站在破旧的黑板前,声音低沉但充满力量,“我们接到了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。”
他详细介绍了穿插任务的内容和要求。会场里静得连呼吸声都能听见。每个人都明白,这是一个九死一生的任务。
371团团长郑希和第一个站起来:“师长,我们团打头阵!”
372团团长张景耀不甘示弱:“凭什么你们打头阵?我们372团的战斗力不比你们差!”
370团团长也要争,三个团长差点吵起来。
“都别争了!”苏克之一拍桌子,“这次是整个师一起上,谁也跑不了。371团、372团为第一梯队,370团负责预备队和阻援。都给我打起十二分精神来,这一仗,关系到整个战役的成败!”
他走到地图前,开始部署具体战术:“我们的路线是这样的,从道城岘突破,然后沿着这条山沟急行军,目标是济宁里。这一路上,我们要避开大路,专走小路。宁可多走十公里,也不能被敌人发现。”
“师长,”参谋长提醒道,“这条路线要翻越三座大山,还要渡过两条河。现在河面都结冰了,但冰层厚度不均,很危险。”
“危险也要走,”苏克之斩钉截铁,“记住,我们是去掏敌人的心窝子。只要我们成功了,整个南朝鲜军队就会崩溃。这个险,值得冒!”
05
1950年12月31日,除夕夜。
当中国内地的人们正在准备迎接新年的时候,朝鲜战场上,第三次战役打响了。
124师的出发地点在道城岘以北的一片松林里。八千多名战士静静地蹲在雪地上,每个人都反穿着棉衣,白色的里子朝外,与雪地融为一体。这是苏克之的主意,为了最大限度地隐蔽行踪。

气温已经降到零下三十五度。战士们的眉毛、胡子上都结了一层白霜,呼出的气立刻变成白雾。为了防止冻伤,每个人都在不停地搓手跺脚,但动作都很轻,生怕发出声音。
苏克之蹲在队伍最前面,眼睛紧盯着前方。按照计划,晚上八点,友邻部队会发起正面进攻,吸引敌人的注意力。然后124师趁机从侧翼突破。
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。七点五十分,远处传来隐约的炮声。八点整,炮声骤然密集起来,整个天空都被照亮了。
“出发!”苏克之低喝一声,第一个冲了出去。
八千多人的队伍像一条白色的长龙,在雪地上快速前进。没有人说话,只有急促的呼吸声和踩雪的沙沙声。
道城岘的敌人正被正面的猛烈进攻吸引,没有注意到侧翼的动静。124师顺利通过了第一道防线。但苏克之知道,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。
午夜时分,部队来到一条山谷。这条山谷是通往济宁里的必经之路,但也是最危险的地方。山谷两侧都是陡峭的山壁,如果被敌人发现,整个部队就会成为瓮中之鳖。
“停止前进!”苏克之举起手。他派出侦察兵先行探路,自己则带着几个参谋爬上山坡,用望远镜观察地形。
月光下,山谷深处隐约可见几处火光。那是敌人的哨所。
“师长,要不要先打掉这几个哨所?”参谋长建议。
苏克之思考了一会儿,摇摇头:“不行,一旦开火,就会暴露我们的位置。我们从旁边绕过去。”
“旁边?”参谋长吃了一惊,“旁边都是悬崖峭壁,怎么走?”
“就是因为是悬崖峭壁,敌人才不会防守。”苏克之的眼中闪着光芒,“通知部队,准备攀岩!”
这个决定让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。在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中,攀爬覆满冰雪的悬崖,稍有不慎就会摔得粉身碎骨。但军令如山,没有人敢违抗。
战士们用绑腿布连接成绳索,最敏捷的侦察兵先爬上去,然后放下绳索,其他人依次攀爬。每个人都屏住呼吸,手脚并用,一寸一寸地向上爬。
突然,一个战士脚下一滑,眼看就要掉下去。旁边的战友一把抓住他,两个人都悬在半空中。下面的战士赶紧托住他们,总算化险为夷。
两个小时后,全师八千多人奇迹般地翻越了悬崖。当他们出现在济宁里城外的时候,守城的南朝鲜军队完全没有防备。
06
1951年1月1日凌晨3时30分,新年的第一天。
124师如神兵天降般出现在济宁里。这座小城是南朝鲜军队的重要补给基地,囤积着大量的弹药和粮食。城里的守军做梦也没想到,中国军队会出现在他们的大后方。
372团团长张景耀率领部队悄悄摸进城里。街道上静悄悄的,只有几个哨兵在打瞌睡。张景耀做了个手势,几个侦察兵像猎豹一样扑过去,无声无息地解决了哨兵。
“快,占领弹药库!”张景耀低声命令。
一个连的战士冲进弹药库,里面堆满了美式武器和弹药。战士们的眼睛都亮了,这些天他们一直在为弹药发愁,现在可好了,敌人送上门来了。
与此同时,371团从另一个方向进城,直奔敌军指挥部。指挥部里,南朝鲜军的军官们还在睡梦中,突然被冲进来的中国士兵惊醒。

“不许动!缴枪不杀!”371团的战士用生硬的朝鲜语喊道。
一个南朝鲜上校想要反抗,刚掏出手枪就被一个战士一枪托砸晕。其他人见状,乖乖举起了双手。
就在124师占领济宁里的同时,正面战场上,志愿军主力部队已经突破了三八线。美军和南朝鲜军队兵败如山倒,开始全线撤退。
但他们没想到的是,退路已经被切断了。
上午7时,第一批溃兵出现在济宁里北面的山口。这是南朝鲜第32团的一个营,他们丢盔卸甲,狼狈不堪。
苏克之早就在山口布置了伏兵。当敌人进入伏击圈后,一声令下,机枪、步枪、手榴弹一齐开火。敌人像割韭菜一样倒下,剩下的人跪地求饶。
“师长,抓了三百多俘虏,怎么办?”370团团长跑来请示。
“派人看管起来,给他们饭吃。”苏克之说,“记住,优待俘虏,这是我们的政策。”
但麻烦的事情很快就来了。中午时分,两架美军飞机出现在济宁里上空。这是例行的侦察飞行,如果被他们发现城里已经易手,124师的位置就会暴露。
张景耀急中生智,从俘虏中问出了美军的联络信号,然后让懂英语的翻译在地面摆出信号。美军飞行员看到熟悉的信号,以为一切正常,绕了一圈就飞走了。
“好险!”张景耀擦了擦额头的冷汗。
下午,更大规模的溃军出现了。这次来的是南朝鲜第31团和第36团的残部,还有两个炮兵营,总共有四千多人。
苏克之知道,这是一块硬骨头。他迅速调整部署,命令371团和372团正面阻击,370团从侧翼包抄。同时,他派人与友邻的66军联系,请求协同作战。
战斗异常激烈。敌人知道后路被断,拼命想要突围。他们集中所有的火力,向124师的阵地猛攻。一时间,枪炮声震天动地,硝烟弥漫。
“顶住!一定要顶住!”苏克之在前沿阵地大声喊道,“援军马上就到!”
关键时刻,66军的一个团及时赶到,从敌人背后发起攻击。腹背受敌的南朝鲜军队终于崩溃了,纷纷缴械投降。
这一仗,124师歼敌两千余人,俘虏一千八百多人,缴获大批武器弹药。更重要的是,他们成功切断了敌人的退路,为主力部队的推进创造了有利条件。
07
1月4日,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,一举攻克汉城。这个消息震惊了全世界。
美国总统杜鲁门紧急召开内阁会议。会议室里愁云惨淡,国防部长马歇尔脸色铁青地说:“先生们,我们必须面对现实。中国人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落后,他们的战斗意志和战术都远超我们的预期。”
“麦克阿瑟将军怎么说?”杜鲁门问道。
“他要求使用原子弹。”马歇尔苦笑,“但我认为这不现实。如果我们使用原子弹,苏联人不会坐视不管的。那样的话,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了。”
杜鲁门沉默了很久,最后说:“告诉麦克阿瑟,准备撤退到釜山。同时,通过外交渠道探探中国人的口风,看看有没有谈判的可能。”
与此同时,在汉城的总统府里,彭德怀正在给毛泽东发电报:
“主席:遵照您的指示,我军已胜利攻克汉城。第三次战役取得完全胜利,歼敌5万余人。实践证明,您的决策完全正确。如果我们当初接受了停战建议,就不会有今天的胜利。”

毛泽东收到电报后,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他对周恩来说:“彭老总还是明白了。战争有时候就像下棋,该进的时候必须进,犹豫不决就会满盘皆输。”
“主席英明。”周恩来说,“现在全世界都看到了新中国的力量。很多原本观望的国家,都开始主动接触我们了。”
毛泽东点点头,但随即又说:“胜利了更要保持清醒。美国人不会甘心失败的,他们一定会反扑。告诉彭德怀,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。”
08
战后,苏克之被授予一等功。在庆功会上,他说了一段话,让所有人都深受感动:
“这个胜利,不是我苏克之的,是全师八千多名战士用血和汗换来的。我想起了那些牺牲的战友,他们有的连名字都没留下。他们为什么要牺牲?不是为了当英雄,而是为了让祖国不再受欺负,让我们的孩子能在和平的环境中长大。”
他停顿了一下,眼睛有些湿润:“我还要感谢毛主席。说实话,当时接到必须打过三八线的命令时,我心里也犯嘀咕。我们确实太困难了,战士们连饭都吃不饱。但事实证明,毛主席看得比我们远。如果不打这一仗,美国人就会认为我们软弱可欺,以后的仗会更难打。”
1975年,苏克之将军去世前,他的儿子问他:“爸爸,您一生最自豪的是什么?”
苏克之虚弱地笑了:“是在朝鲜,带着124师的战士们,打过了三八线。那一仗,我们让全世界知道,中国人民站起来了,再也不会跪下了。”
多年以后,美国军事历史学家约翰·托兰德在其著作《漫长的战斗》中写道:
“1950年冬天的朝鲜战场,是美国军事史上最黑暗的时刻之一。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次战役的胜利,特别是124师在济宁里的穿插,展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军事素养和牺牲精神。这支部队在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中,翻越悬崖峭壁,奇袭敌后,创造了军事史上的奇迹。”
“更让人深思的是毛泽东的战略眼光。当所有人都认为应该在三八线停战时,他坚持要打过去。事后证明,这个决定改变了整个朝鲜战争的走向,也改变了东亚的政治格局。”
历史学家黄仁宇则认为:“第三次战役的胜利,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,更是意志的胜利。它告诉世界,一个贫穷但团结的国家,可以战胜一个富裕但傲慢的国家。这个教训,至今仍值得深思。”
而在中国军事博物馆里,有一面锦旗,上面写着“济宁里英雄团”。这是372团的战士们用缴获的敌人军旗改制的。锦旗虽然已经褪色,但那段历史却永远鲜活。
每年的1月4日,汉城光复纪念日,总会有一些白发苍苍的老兵来到博物馆。他们静静地站在锦旗前,眼中含着泪水。他们中有的人参加过那次伟大的穿插,有的人在正面战场浴血奋战。
岁月如流水,当年的青春少年如今已是耄耋老人。但每当回忆起那个寒冷的冬天,回忆起在冰天雪地里的急行军,回忆起攻克汉城时的激动心情,他们的眼睛依然会发光。
因为他们知道,他们参与书写了中华民族复兴史上最壮丽的篇章。他们用青春和热血,向世界宣告:中国人民站起来了!
这,就是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的故事。一个关于勇气、智慧和牺牲的故事。一个永远不应该被遗忘的故事。
【参考资料来源】
《彭德怀军事文选》,解放军出版社《抗美援朝战争史》,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《志愿军第42军征战纪实》,辽宁人民出版社苏克之将军回忆录《血战三八线》《毛泽东军事文集》第六卷,中央文献出版社
淘配网-如何杠杆炒股-股票在线配资-全国前10正规配资公司平台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安全炒股配资门户特朗普在第一次总统任期结束后的数月间
- 下一篇:没有了